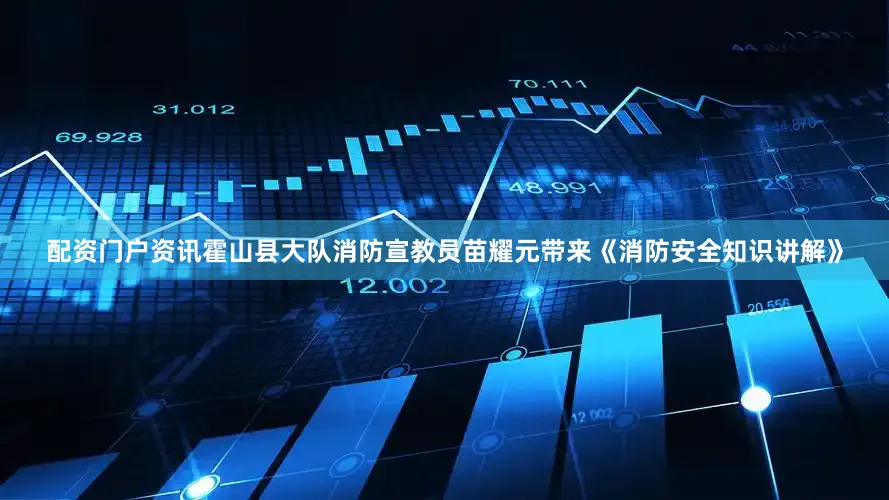一、拆解资料:定义和测量
梁惠王说:「我对国家很尽心。河内发生灾荒,就把部分百姓移到河东,把粮食运到河内。河东发生灾荒的时候也是。观察邻国的政务,没有人和我一样用心。但是邻国的居民不减少,我的居民不增加,这是为什么呢?」孟子说:「大王喜欢战争,请让我用战争做比喻。如果有士兵,在击打战鼓,双方兵刃相交的时候,丢弃盔甲拖着兵器逃跑。有的跑了一百步后停止,有的跑了五十步停止。结果跑了五十步的人嘲笑跑了一百步的人,您觉得如何?」「当然不可以,他只不过没有跑到百步而已,他还是逃跑了。」
这是《孟子.梁惠王章句上》中著名的段落,也是成语「五十步笑百步」的来源。在这段对话中,梁惠王举出「资料」质疑孟子的「论点」也就是:如果施行仁政,那么百姓就会增加。根据他的资料,他施行仁政,可是百姓却没有增加,其他国家不施行仁政,百姓也没有减少--透过一份资料,同时从正反两个层面进行质疑,梁惠王这资料用的不错。那么孟子是怎么回应的呢?他的做法是,质疑梁惠王对「仁政」的定义。在士兵的例子里面,逃跑就是逃跑,不会因为跑得近或者跑得远而有差别,这是因为事情的本质不会因为程度而改变。所以,虽然梁惠王做得比邻国还要多,他的行为还是称不上「真正的仁政」。当然,这么进行攻击后,孟子也很负责任的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仁政,大破后需要有大立,如果只是单方面拆解却不愿意论证,那么说服力终究有限。在《孟子.梁惠王章句下》孟子故技重施,只是这次就比较草率。齐宣王问说:「商汤流放夏桀,武王讨伐纣王,有这回事吗?」孟子说:「文献上看起来是有的。」齐宣王问:「臣子杀害君主,这样可以吗?」孟子说:「嗯?败坏仁的人叫『贼』。败坏义的叫『残』。残、贼的人就『独夫』。我只听说有独夫纣被杀了,没听说过弑君这种事。」相比梁惠王,齐宣王的水准比较低,孟子的回答也比较随便。气势少了,游刃有馀的潇洒却多了,说服力却没有减少太多,这就是因应对手并且做出不同判断的工夫。另外,包含定义在内,拆解资料的方向总共有四个:定义、测量、样本、推论。通常来说,我们很难检验资料的样本,因为就算是论文,也只会交代抽样方法,而不会真正呈现所有样本。而推论可以独立成另外一个课题,因此接下来,我们就谈谈使用「测量」来拆解资料的方式,这是在《孟子.公孙丑章句下》的例子。
燕国人叛乱,齐王说:「我觉得自己很惭愧,对不起孟子」陈贾说:「大王不要心烦,你觉得自己和周公相比,谁比较有仁义和智慧?」齐王说:「靠!你这什么问题?」陈贾说:「周公派遣管叔去监督殷人,管叔却带着殷人叛乱。如果周公早就知道他会叛乱,那麽这麽做就是不仁。如果他不知道,就是不智。周公都不能完全具备仁和智,何况是大王呢?请允许我见到孟子的时候替您解释。」陈贾见到孟子后问他:「周公是什么人?」孟子说:「古时候的圣人。」陈贾说:「周公派管叔监督殷人,结果管叔和殷人一起叛乱,有这回事吧?」孟子说:「嗯哼。」陈贾说:「周公是知道他会叛乱还派他去吗?」孟子说:「他不知道吧。」「嘿嘿,那么你的意思是圣人也会犯错喽?」孟子说:「周公是弟弟,管叔是哥哥。周公的过错,不是情有可原吗?而且古时候的君子,犯了错就改正;现在的君子,犯了错却继续不改。古时候的君子,他的过错好像日蚀、月蚀,人民都可以看见;等到他改正后,人民都仰望他。现在的君子,岂止通融错误?甚至还为错误辩解。」
在这段故事开头,齐王对燕人的叛乱感到很苦恼,陈贾举出「资料」告诉他,犯错不用苦恼,就连周公也会犯类似的错误。面对这份资料,孟子并不是质疑「错误的定义」,而是「测量的精度」,换句话说,同样是错误却有大错误和小错误,把他们混为一谈得出的结果肯定会非常偏颇。此外,孟子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两种错误的不同,拆解后还有论述,再次证明了孟子的正气浩然。二、比较价值:前提和缺失比较孟子谒见梁惠王。王问:「老先生,你不远千里而来,应该是有什么利益要带给我的国家喽?」孟子回答说:「大王何必开口就谈利益呢?只要有仁义就够了!大王问『要怎么对我的国家有利?』大夫问:『要怎么对我的封邑有利?』士人平民问:『要怎麽对我自己有利?』上下互相争夺利益那国家就危险了。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中,杀掉国君的肯定是有千辆兵车的大夫;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中,杀掉国君的肯定是有百辆兵车的家族。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中有千辆,千辆的国家中有百辆,实在不能说不多。如果先谈利后谈义,他们不抢夺更多是不会满足的。相反的,没有重视仁却遗弃亲人的,也没有重视义的人却不先考量君主的。所以大王只要谈仁义就好,何必谈利呢?」这是《孟子.梁惠王章句上》著名的「王何必曰利」,在这段对话里头,孟子进行的是「仁义/利益」两者的价值比较。要成功进行价值比较,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:找到对方价值的前提,然后在阐述自己价值的同时,兼容对方的前提。梁惠王谈利益,可是他的前提是:能够保有利益。没有这个前提,后面谈再多都是空话,因此孟子针对这个前提直接进攻,先是论述追求利益如何破坏这个前提,然后反过来,论述仁义又是如何能够稳固现有的利益。如此正反论述搭配排比修辞,孟子对进行的「仁义/利益」比较可说是气势万钧、无懈可击。「寻找前提」这个方法,不只在进攻的时候好用,防守的时候更好用。在《孟子.离娄章句上》有这么一段对话:淳于髡问:「男女之间不亲手递送物品,这是礼吧?」孟子说:「这是礼。」淳于髡问:「那如果嫂嫂溺水了,要不要用手救她呢?」孟子说:「嫂嫂溺水不救,这是豺狼。男女之间不亲手递送物品,这是礼节。嫂嫂溺水用手救她,这是权变。」
在这里,淳于髡透过嫂嫂溺水的状况,要求孟子比较「性命/礼节」这两个价值,孟子要守护礼同时兼顾嫂嫂的性命,在这里他有两个选择:寻找性命的前提,或者寻找礼节的前提。进可攻,退可守,孟子选择防守,用「权变」来作为兼顾两者的答案。另一个例子是《孟子.尽心章句上》桃应的问题。
桃应说:「舜是天子,皋陶是法官,瞽瞍杀了人,该拿他怎么办。」孟子说:「让皋陶把他抓起来喽。」「那么舜不阻止吗?」孟子说:「舜怎么能阻止呢?皋陶的权力是他授予的啊。」「那么舜应该拿他老爸怎么办?」孟子说:「对舜来说,抛弃天下就和抛弃破草鞋一样。他会偷偷的背着父亲逃跑,躲到海边去,后半生开开心心的活着,忘了天下。」
桃应的要求孟子比较的是「孝顺/法治」这两个价值。和前面处理礼节的方式相似,孟子也回过头去寻找法律的前提,因此他认为以抛弃天下作为代价,带着父亲逃跑是最好的选择。当然,淳于髡和桃应都可以进一步询问孟子「权变」的标准,也就是礼节和法治的前提。可惜淳于髡没问,桃应不问,孟子也没说。但是不用他说,大家应该也都知道,在法制和礼节背后的是什么。最后要谈的是:「缺失性比较」,也就是全有全无的比较。这是《孟子.告子章句下》:任国有人问屋卢子:「礼节和吃饭哪个重要?」屋卢子说:「礼节重要。」「娶妻和礼节哪个重要?」屋卢子说:「还是礼节重要。」那个人说:「如果拘泥礼节就会饿死,不遵守礼节却可以得到食物,还要遵守礼节吗?如果按照『亲迎礼』就娶不到妻子,不按照『亲迎礼』反而可以娶到妻子,还要遵守亲迎礼吗?」屋卢子回答不出来。隔天到邹国,把事情告诉孟子。孟子说:「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难的?不测量本来的高低,却只比较末端,这样一来木块也能高过楼顶啊。我们说金属比羽毛重,难道是衣带钩的金属和一整车的羽毛比较的结果吗?拿吃饭最重要的部分和礼节最不重要的部分比较,那何止吃饭重要?拿娶妻最重要的部分和礼节最不重要的部分比较,那何止娶妻重要?你回去问他:『扭断哥哥的手臂抢他的食物就能吃到饭,不这么做就没饭吃,你会这么做吗?爬过东边的牆去侵犯他家的女儿就可以得到老婆,不这么做就娶不到妻子,你会这麽做吗?』」在这段对话中,任人比较「礼节/吃饭」以及「礼节/娶妻」的方式,是取食色之重对比上礼之轻,或者说:选了礼节就没有饭可以吃、没老婆可以取,彼此是全有全无的零合关系,也就是所谓的「缺失性比较」。面对「缺失性比较」唯一的回应手段,就是指出对方正在使用缺失比较,并且自己也使用缺失比较,让观众知道这样的比较没有意义。这个价值比较的策略,基本上是所有人都会使用的「泥巴仗战术」,意思是明明知道对方肯定有办法破解,却还是不得不使用,因为你不使用对方就会用,到时候吃亏的只会是自己,可以说是辩论比赛中的恶性竞争。三、类比论证:应用和拆解孟子对齐宣王说:「假如大王有个臣子,把妻儿托付给朋友,自己到楚国游历。他回来的时候,却发现自己的妻儿在挨饿受冻,该怎麽对这个朋友?」齐宣王说:「抛弃这个朋友。」孟子说:「狱官不能管理下属,应该怎么做?」齐宣王说:「撤换他。」孟子问:「国家如果治理不好,又应该怎么做呢?」齐宣王转头看了看左右的人,然后开始谈论其他话题。
论证命题的方法有两种,分别是:演绎法以及归纳法。严格来说,真正在逻辑上有效的只有演绎法,但是日常生活中,我们更常使用归纳法,用过去的经验预测未来、部分的样本推测全体。归纳法的重点在于:找出事物的规律,也就是观变思常。而「类比论证」则是归纳法的一个类型:透过归纳思维,我们发现某类事物都服膺某个规则,因此在碰到另一个同样属于该类的事物时,我们就会推测它应该也服从相同的规则,这就是类比论证的运作方式。而在这段对话中,孟子举出的都是某个身份(类别)的人,违反本分后该如何处置(规则)的例子。既然朋友和士师在违反本分后,都应该被抛弃,那么君王没有做好本分,又应该怎么处置呢?孟子的类比层层递进而且举例洽当,所以使得齐宣王没有办法有效回应。可是在实际运用的时候,需要注意两个问题:第一,对手不一定会配合回答每个类比;第二,拿来类比的例子如果相似度不够,很容易被对方进行切割,进而失去效果。陈臻在《孟子.公孙丑章句下》就犯了这个错误。
陈臻问说:「以前在齐国,齐王送你一百镒(两百两)金子你不接受;在宋国的时候,送你七十镒你却接受了;在薛的时候,送你五十镒你也接受前面不接受如果是对的,那麽现在不接受就是错了;现在接受如果是对的,那么过去接受就是不对的,您必定要在这两个状况选一个。」孟子说:「都对。在宋的时候,我将要远行,远行必须要路费,对方说『送我路费。』我为什么不接受?在薛的时候,我要防备盗贼,对方说『听说你要防备盗贼,那送点钱给你买兵器。』我为什么不接受?但是在齐的时候,我不需要钱。没有理由却赠送别人钱财,就是收买,哪有是君子却可以被人收买的道理?」宋、薛的国君都要给孟子钱,这同类型的行为,面对同类型的行为,应该要有相同的反应(规则),那么为什么面对齐王的时候,可以有不同的反应呢?陈臻对孟子使用的是个「双刀论证」也就是俗称的「悖论」,对方不管怎么选都会导致自相矛盾的结果。坦白说,他这两刀姿势标准、招式到位只可惜底气不足,让孟子用雄浑的内力强行破招。他说:因为齐和宋、薛的状况不同,因此不能类比。拿来类比例子必定是有同有异,因为如果全部皆同,那就不叫「类比」而是「实证资料」,因此只要能找出其中不同,你也可以和孟子一样,拆解类比轻松上手。然而,最恐怖的状况不是对手不配合,或者类比被对方拆掉。最可怕的状况是:类比被对方挪为己用!在《孟子.告子章句上》告子就被这样打得满头包。
告子说:「人性就好杞柳;义好比杯盘。要使人性有仁义,就像是杞柳成为杯盘。」孟子说:「你能顺著杞柳的本性把它做成杯盘吗?还是要伤害了杞柳后才能做成杯盘?如果要伤害杞柳才能做成杯,那是不是也要伤害人性才能得到仁义。率领天下的人却祸害仁义,肯定都是有你这种言论的人。」告子说:「人性好比湍急的水流,在东边开个缺口就往东流,在西边开缺口就往西流。人性没有善与不善,就好比水流没有东西的分别。」孟子说:「水流确实不分东西,可是它不分上下吗?人性的善,就像水往下流。人没有不善,水没有不往下。你拍打水面可以让水溅过额头,阻挡使它逆流可以流上山坡。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?这是环境造成的结果,就好比你可以使一个人变得不善,两件事情本质是一样的。」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天创网配资-在线配资网站-配资导航网-配资门户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